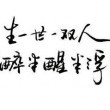–
我,真的有許多沖動和沉思,把那些曾經握過手的“太多”全都裝進那包行囊中,感動超然,
真心地走進任何一塊石頭,一棵樹木,一片片小草,跟它們說說話,
把最樸素的想法告訴給它們,想俯下身子親近每一珠小草和石頭,和那一朵朵野花,
跟它們交交心,敘說著酸甜與冷暖,誰說沉默了意味著就沒有生命的呢?
或許,它們比我的祖輩們都更加年長的呀。都呈現出了縮命似的的接納,
都賦予了一種靈性一般的共同感悟,沒有悲喜的跌宕,
坦誠著一種平平常常的無私與無怨,這種神閑氣定的大氣魄,
–
我們人類那里會有這樣的感受呢?聊到“太多”的話題,
不外乎都在那一圓圈當中而感受罷了;我忍不住要將它與我們的文學圈聯系起來。
文學的“出圈”有沒有可能呢?不得不承認,在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的今天,
這種可能性已然變得微乎其微。當然也不乏反例,比如科幻作家劉慈欣。
從獲得雨果獎的《三體》到改編成電影的《流浪地球》,
他幾乎憑借一己之力,將一直局限在小眾圈子里的中國科幻文學
帶到了尋常百姓面前。難道這不就是他的辛勞與勇氣的收獲?
學習提高,交流進步,創作發表,繁榮網絡,提升素養……

你可能也喜歡Related Posts
眾說紛紜Comments
- 推薦文章
- 最多評論
- 最熱文章
- 最新評論
- 有一種愛只是意外 配樂:白色印記 作者:寒蕭蕭
- 錯愛流年,心為誰碎 配樂:風云榜 作者:紫檀情緣
- 淡淡的憂傷 《黃手帕》吉他配樂
- 哭泣的城市
- 風居住的街道 作者:qiaoqiao0401
- 青春,在破船里沉浮 配樂:悲傷的回憶 作者:辰宇天空
- 姜氏孤兒 《仙劍奇俠傳》配樂
- 【二胡】古人訴離殤《江山此夜》藝術家:河圖
- 幾世情緣 配樂:夜音之殤 作者:草野
- 《倩女幽魂》電視劇原聲配樂
- 《緣之空》優美鋼琴背景音樂《遠い空へ》
- 【鋼琴精選】天籟鋼琴精選合集 100首[百度網盤]
- S.E.N.S. 神思者簡介 (1988-2015全集無損下載FLAC/APE/MP3)
- 《新白娘子傳奇》經典配樂集伴奏集(含配樂無損下載)
- 化作千風守護你 憂傷塤曲
- 《蝶戀》-仙劍奇俠配樂(鋼琴、竹笛、吉他、墨明棋妙等10個版本)
- 芊芊(純音竹笛版)藝術家:周小航
- 【墨明棋妙】《雨碎江南》印象 琵琶 二胡 笛子 洞簫 塤 客緣等9個版本
- 《羋月傳》配樂 - 羋月與黃歇的愛情主題 女聲 哼唱
- 【WordPress技巧】wordpress Tstyle實現Ajax評論(非插件代碼版)